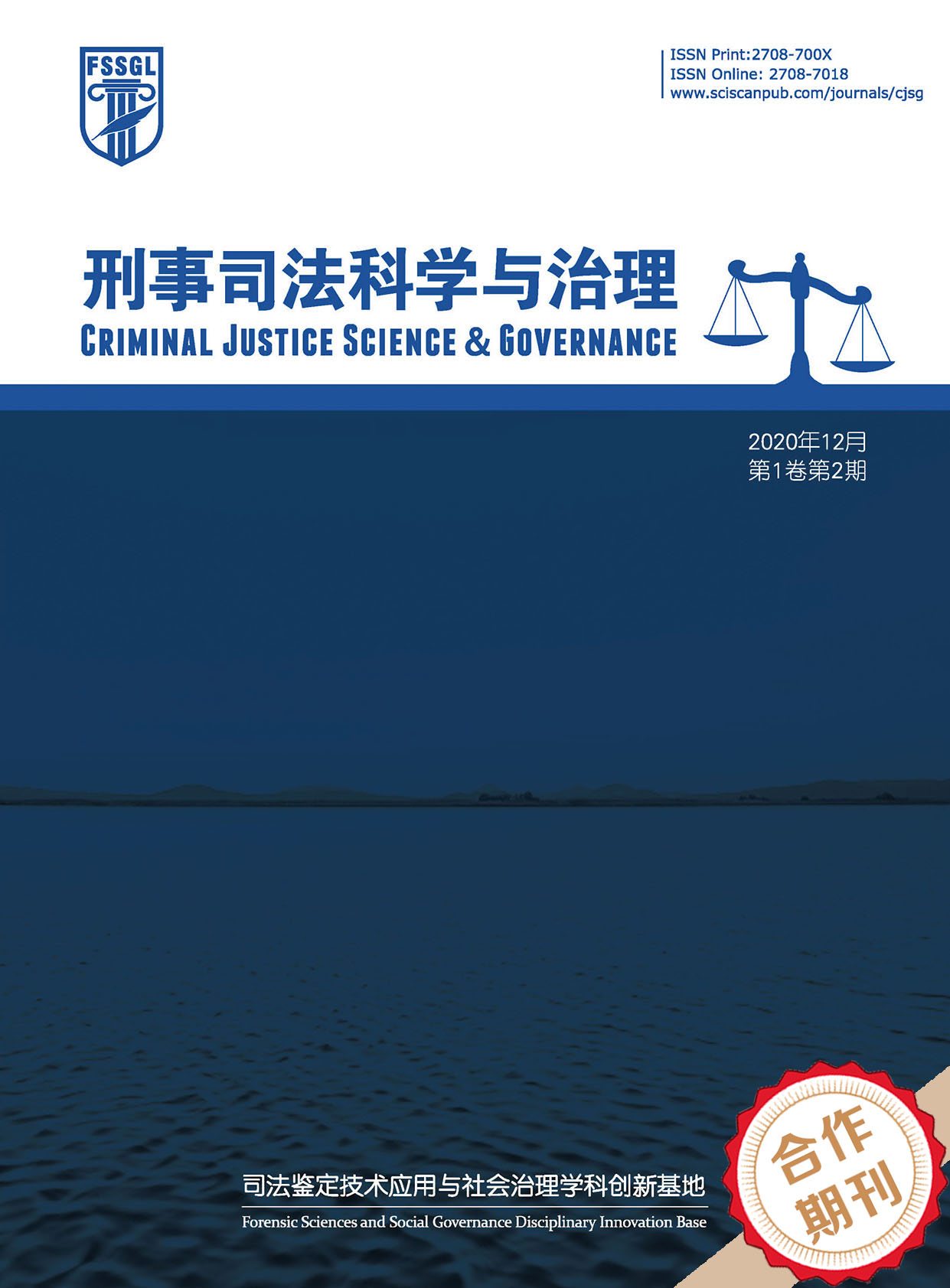Criminal Justice Science & Governance
法医学科体系重构与“全健康”社会治理——后疫情时代法医学科体系重构
Reconstruction of Forensic Medicine System and “One health”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Post-pandemic of COVID-19
- Authors: 何方刚¹³ 陈玲¹ 闫平²³
-
Information:
1.武汉大学,武汉; 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 3.司法鉴定技术应用与社会治理学科创新基地,武汉
-
Keywords:
Forensic medicine; Judicial expertise; One heal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of forensic medicine; COVID-19法医学; 司法鉴定; 全健康; 法医科学技术体系; 新型冠状病毒疾病
- Abstract: During the SARS-CoV-2 pandemics, medical examiners played a professional role and provided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OVID-19 through autopsy, thus named as medical "scout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he discipline and system of forensic medicine in China.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the disciplinary of forensic medicine system, establish an intensive management system of modern forensic medicine center, promote the discipline of forensic medicine to better serve human health and national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Healthy China 2030" and "one health" social governance. 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法医发挥专业优势,通过尸检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诊疗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发挥了“侦察兵”作用。但我国法医学科体系也存在问题,专业设置、教育培训和鉴定管理体系存在不合理的现状和困境。后疫情时代,需要重构法医学科体系,建立集约化现代法医中心管理体系,推进法医学科更好的服务于人类健康和国家法制建设,推进“健康中国2030”实施和 “全健康”社会治理。
- DOI: (DOI application in progress)
- Cite: 何方刚,陈玲,闫平.法医学科体系重构与“全健康”社会治理 ——后疫情时代法医学科体系重构[J].刑事司法科学与治理,2020,1(2):12-18.
当前全社会的注意力仍大量集中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上,我国发挥制度优势,严防死守,把生命安全和健康摆在第一位,竭尽全力挽救生命,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阶段性胜利。但全球疫情的形势依然严峻,未来一段时间内疫情防控将成为常态化状态。非新冠肺炎如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对人民群众生命威胁并没有减弱。一方面,伴有严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者感染新冠病毒后的病死率显著增加;另一方面,在疫情爆发阶段,疫情中的感染风险和疫情防控的医疗资源调集和挤兑,导致常规医疗功能减弱,引发主要慢性非传染病的病死率增加,产生“次生灾害”。后疫情时代,若要更加有效的控制疫情对国民健康和社会活动的严重干扰,减少次生灾害,需要以“全健康(One Health)”理念促进人类健康—动物健康—环境健康协调发展,多学科专业统筹配合,推进社会协同治理。
一、全健康(One Health)概念的起源及阐述
“One Health”是一种多学科交流和协作,共同致力于促进人类健康、动物健康、维护和改善食物安全及生态环境的新理念与实践策略,其需要在规划、政策、立法和研究方面协同作用,最终达到更优化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公众健康效果,所涉及的领域主要包括:人畜共患病控制、食品安全、抗生素耐药性应对、生态环境等。尽管“One Health”是个新名词,但其理念已很早被国际社会认识,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希波克拉底就曾提出的“公共健康依赖于清洁的环境”。19世纪中期,德国医师及病理学家Rudolf Virchow认为人类医学和动物医学间存在联系并提出了“人畜共患病”名词,进入21世纪后,科学家们更注意到人类疾病和动物疾病相似性。2003年William Karesh认为人类、家畜和野生动物健康不能割裂讨论,提出“One Health”名词。近期,国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陈国强院士提出将“One Health”翻译为“全健康”,建议整合完善与健康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层面切实贯彻“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思想,为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二、法医学科对“全健康”社会治理的作用
(一) 新冠疫情期间法医学科的作用
在武汉新冠肺炎爆发、社会恐慌之际,2020年2月16日我国法医学者刘良团队克服各种困难实施了COVID-19死亡全球第一例系统法医尸检,2月份病理学者卞修武院士团队也报道了3例新冠肺炎死亡后多部位微创穿刺的病理发现。此后这些发现写入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七版),对临床诊疗发挥了重要作用。4月初美国法医学者也报道了2例系统解剖案例,5月初德国法医学者回顾研究了新冠肺炎期间系统尸检案例,发现COVID-19血栓发生率高,而且疫情期间部分患者死亡原因不是COVID-19,对疫情期间的公共卫生和疾病与健康管理有重要参考价值。笔者团队也在武汉“封城”及整个疫情期间接受各地公安或疫情防控指挥部委托开展了10余例尸体解剖,为各地科学的解决疫情相关的社会稳定和治理问题发挥了作用。法医和病理学者在直接暴露于病毒“暴风眼”、传染风险极大、尸检条件尚不完备情况下,勇于担当,积极承担尸检任务,寻找病理和病因机制,尸检病理学发现,逐步完善了的COVID-19的认识,协助病情判断和治疗,为此类影响全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的诊疗提供了第一手重要依据和资料。同时法医学者通过尸体解剖,探究病毒在体内的分布情况,也对疫情期间“复阳”问题的原因判断和粪口传播问题给以有价值的分析,解除了民众的困惑和恐慌,稳定社会抗疫进程。
(二)法医学科对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的作用
我国绝大多数尸体解剖由法医完成,包括刑事案件、涉及赔偿的民事案件、重大灾害事故、交通事故、医疗纠纷、职业病相关的死亡、吸毒相关的死亡及不明原因的死亡等。这些尸检资料和样本材料为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其他生命科学研究、疾病的诊疗提供了基础和支撑。随着人类活动的多元化扩张和生态环境的变化,各类新发、未知疾病的不断出现,在环境改变相关疾病(环境法医学)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法医学尸检研究是填补医学研究空缺的重要手段,从全健康社会治理(包括公共卫生、公众健康、环境健康等)的角度,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法医学科的作用。
猝死的原因、机制和预防一直医学重要问题,法医病理学家对不明原因猝死机制、分子遗传学研究一直处于各类医学的领跑和前沿,为猝死的预防和健康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医疗纠纷尸检也是我国法医工作的重要内容,这些尸检工作对于医疗过程中疑难病例寻找病变和死因、解决临床问题和医疗纠纷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和依据。客观上,法医解剖也在医学教学中的发挥“活”标本作用,是医学研究中最真实样本来源。
(三) 法医学科对死亡和疾病信息、公共卫生与健康的作用
法医学是医学学科,也是为司法服务的一门鉴识科学,更重要的是为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公共卫生服务。目前我国的死因统计、疾病监测的准确性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法医学结合法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建立了死亡原因的分类方法,对死因推断更加准确,有利于完善我国死因和疾病谱的准确统计、更好推进健康管理和疾病预防政策的制定。这次全球蔓延的疫情中法医学尸检对疾病的认识、死亡原因构成的判断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在“全健康”理念的社会治理中,法医学科在死亡原因调查、重大传染性疾病的发现和诊断、公共卫生事件(法医毒理学、毒物学)的调查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法医学对现代法制社会治理和法学、社会学科的作用
法医学是研究并运用医学知识解决有关司法问题的综合学科。法医学的研究和鉴定工作在人身损害残疾程度的评价体系和规范、医疗纠纷的预防与控制方面的作用必不可少,也为我国保险理赔、社会稳定、医患关系的和谐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当代法医学经历了近四十年的快速全面发展,已由边缘学科逐渐发展成拥有独立的基础理论和完备的分支学科体系,支撑领域和解决的涉法专门性问题越来越广泛,对我国司法审判实践的贡献越来越大。
三、法医学科的现状、挑战及对公共健康发展的影响
在全球新冠疫情期间,法医学科对新冠肺炎的诊疗和减少恐慌、维持社会稳定中发挥了“侦察兵”作用。但随着法制社会发展、公共卫生和健康社会需求,法医学科也面临挑战和发展机遇,学科体系需要重新审视和构建,从而更好的发挥作用。
(一)教育培训和学科设置不合理
在法医学教育培训体系上,我国法医学科体系不同于现代医学、法医学起源较发达的欧美、日本等国家或地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国首创了在高等医学院校开设法医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这种“短而快”法医人才培养模式解决了特定历史时期法医人才数量不足问题,在我国法制化建设的快速发展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发展40多年来尚未建立严格规范的专业人才资格认证制度、完善的毕业后教育培训体系以及“专家型”人才培养模式。
在学科设置上,法医学没有真正置入“全健康”理念的医学系列,将法医学科定位于特种医学的一个分支,证据意识教育较强,但医学理论学习和实践能力培训偏弱,这种设置导致我国法医学科被医学学科边缘化;尤其法医病理、法医临床学科与临床医学专业教学培训体系脱节,导致法医病理学和法医临床学科成为明显区别于临床医学的特殊学科。法医专业学生虽然学习内容涵盖了临床医学专业全部内容,但医学知识学习“全而浅”。由于学生缺乏真正有效的临床医学学习和培训经历,他们对损伤和疾病的理解不够系统、深入,在法医鉴定工作中对死因分析、医疗行为评价、伤残评定可能出现系统偏差,对损伤、伤残鉴定标准中法定条款的机械理解、生搬硬套,容易出现错误。另外,法医专业学生不能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无法获得执业医师资格,也严重影响了法医专业学生学习临床和基础医学知识的积极性。基于专业门槛限制,不愿从事法医职业的法医专业学生不能从事临床医学,而少部分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在从事法医职业时因为未受过法医专业基础、系统的教育培训,其后续培训时间更长。
另一方面,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法医学教育未普及甚至缺失,导致临床医学毕业生或执业者欠缺法医学知识,对于执业医师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和潜在的执业风险缺乏了解,对执业中面对的法律问题无法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对防范医疗纠纷风险、提高医疗质量非常不利。这些问题既不利于临床医学和法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是影响法医学科长远发展的瓶颈。
(二)对国家公共卫生和健康体系建设的影响
在医学史上法医学为发现新发疾病和公共卫生事件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人类活动扩张和环境的变化,环境、职业或毒物相关的死亡、大型突发事件引起的群体性死亡以及传染性疾病相关的死亡将会越来越多,这些都涉及到公共卫生和公众健康问题,若要清楚获取死亡原因或追溯病因,需要具有丰富经验的法医学专家、临床医学专家、流行病专家、毒理专家配合,并需要结合死因调查、以及生物、理化等知识分析才能发现新疾病的特点,促进新发疾病的诊疗、为疾病的预防、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但现在独立设置、被边缘化的法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导致法医人才的培养重心偏向于为刑事案件的侦查服务,其知识体系越来越难以胜任死因和疾病诊断工作,并且有恶性循环的趋势。这些现象的导致法医成为只懂破案的医学“侦探”,背离了医学“专家型”人才培养模式。
目前我国死亡证明书的签发平台存在不科学统一问题,致使疾病和死亡信息的统计准确性也影响我国疾病和人口健康的管理。在美国等法医体系发达的地区,除了医院内因疾病死亡的由医生签发死亡证明(死亡原因明确)外,其他各类死亡均由法医病理学家或验尸官签发死亡证明并明确死亡原因,对有疑问者实施解剖,这既可以保障对全国人口死亡原因和疾病谱的准确统计分析,也可及时发现人群中新发异常疾病并及时处理。笔者访学的马里兰州(人口六百余万)法医中心,每年审核签发死亡证1万余例,其中5千余例需系统解剖,包括大量的中毒和猝死病例;另外其通过尸检也建立了较完备的组织库(脑、心脏等)。
交通事故死亡原因的判断和研究也是法医学鉴定和研究的重要内容,这对受伤死亡人员损伤特点的研究,提出对车内人员、行人的保护的建议,促进工业部门研发生产更安全的交通工具,加强了公共安全,这也符合《“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要求。
(三)法医司法鉴定管理体系和信息化不统一
从法律和政策层面,司法鉴定系统没有统一的宏观管理部门,不同部门的鉴定管理模式不同、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导致死亡和疾病诊断难以统一规范,甚至出现大量错误。以法医学科的核心专业法医病理专业为例:(1)在人员分布上,绝大部分从业人员为警察系统内的侦查技术人员且系警察身份,主要精力是现场调查而不是法医专业工作,专业上也基本只开展命案大体尸检(多数只是结果导向性的局部解剖),其死亡案件信息属于公安管理系统;(2)院校法医病理工作者,有专业优势,但基本工作模式是“游击战模式”,哪里需要尸检就去哪里,大部分尸检在各地殡仪馆进行(解剖室条件简陋),由于条件限制,尸检程序很难标准化、规范化,其死亡和疾病信息管理纳入司法行政管理系统;(3)社会鉴定机构的大部分法医病理执业人员仅仅只能完成病理尸表检验和大体解剖的工作,不能胜任组织病理学工作,院校和社会鉴定机构的涉及的死亡和疾病信息管理纳入司法行政管理系统;(4)高等院校或医院的普通病理工作者基本限定于外科病理,很少能够开展系统的病理尸检工作。这种分散、粗放式法医司法鉴定工作和管理模式是常态,导致我国法医学鉴定和研究的科学性大打折扣。
人口疾病和死亡信息是国家制定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政策的重要参考。目前分散、粗放式法医司法鉴定管理模式,导致法医鉴定中涉及的死亡和疾病信息(如传染病、重要罕见疾病、死亡信息等)也没有纳入国家卫生健康管理部门的信息管理系统中,会导致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和安全事件不能正常纳入国家整体健康管理体系,影响国家“全健康”治理模式的实施和研究。
这次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COVID-19)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病理尸检对明确病变特点、病毒分布和靶点及作用机制非常重要,但我国因为法医司法鉴定管理体系不完善、条块分割的原因。我国作为疫情发现最早的地区,分散的开展了一些尸检,但无法统一、规范、标准化、系统的分析相关数据。由于不同于德国、美国等法医学者的报道价值,我国的循证医学价值和科学性大打折扣,鉴定和研究水平不能走向更高的台阶,留下很多遗憾。因此,上述问题的解决,我国就需要构建更科学的现代法医学科体系。
四、法医学科体系构建的模式
目前我国法医系统为多龙治水状态,条块分割明显,既利于法医学科的发展,也不利于法医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协同发展,更不利于调查和发现新发疾病和公共卫生健康事件。因此,我国亟需构建现代法医体系。
(一)法医学与法庭科学概念不清晰
国际惯用概念中,法庭科学(Forensic Science)是指运行科学知识解决法律问题的学科,其学科领域包括医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环境科学、人类学等学科;法医学(Forensic Medicine或Legal Medicine)是运用医学专业知识解决死亡原因、死亡时间、损伤、伤残或其他法律问题的学科。法庭科学比法医学概念广泛,前者包含后者。我国的法医学概念是指应用医学、生物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技术,研究并解决法律实践中有关医学问题的一门医学科学,类似于国际通用的法庭科学概念,导致法医专业人才学习的知识“全而浅”,不符合“精英化”“专家型”法医学人才的培养和执业需要。
(二)法医学科教育培训体系重构
目前国内的法医学专业设置是历史的产物,因为“全而浅”的培养模式,导致法医专业培养的学生医学专业基础不牢、知识面窄,而法律知识也仅熟悉皮毛。这种体系中培养的人才,因医学知识局限,不利于对死亡案件中疾病的准确诊断、发现和死因分析,不利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实施和“全健康”社会治理,不利于普通高等教育体系中大学生“通识教育”培养,而且知识的局限性也导致就业局限,被临床医学专业排除在外。
法医学人才要走“精英化”“专家型”人才之路,必须让法医专业教育回归大医学专业(可以设置临床医学专业法医学方向),经过医师考试获得执业医师资格。若要取得法医鉴定人资格,需要进一步参加相关的法医知识和法律培训,考核合格后授予法医鉴定执业资格。这样通过后续的继续教育和培训模式转化为法医司法鉴定人,既保证了法医鉴定人的厚基础、宽知识面的专业能力和医学素养,也能更好发挥和体现法医鉴定的严谨、客观、公正的司法属性,促进法医鉴定人的“精英化”“专家型”人才培养模式。以临床医学专业分科为例,临床医学专业中外科专业不可或缺,但在医学专业教育中没有将外科独立设置,而是5年大学通识教育后,经过规范化培训或研究生阶段学习确定专业,再通过后续不断的培训、经验积累才可以成为合格的外科医生。
(三)法医司法鉴定体系重构模式的建议
随着社会法制进步和法医学的发展,法医不能再继续仅仅依靠眼睛观察的“土埂火种”检验鉴定模式,很多损伤和疾病的准确判断需要结合死后影像学检查(CT、磁共振等),各种环境毒物中毒、新型毒品中毒的发现需要精密的检验检测设备,标准化的尸体解剖和法医检验过程需要规范化、条件完备的场所,所以我国法医学科要想可持续的发展就需要建立现代化、集约化的法医司法鉴定中心。集约化的司法鉴定中心包含病理检验、理化检验、生物和痕迹物证检验、影像学、电生理、辅助诊断等仪器设备,具备条件的司法鉴定中心可以集成车辆痕迹检验和法医检验,建立交通事故司法鉴定研究机构。
法医学鉴定不同于其他法庭科学鉴定,不仅是关系到单个司法案件的科学、公平和正义,而且关乎公共卫生与健康、疾病与死亡管理等问题,应实行严格的特许,以公益事业单位的模式管理,根据地域和人口数量,分级分类设立独立运行的法医司法鉴定中心/所。法医中心同时进行地区死亡病例审核和信息登记管理,服务公共卫生和大健康,也有助于完善人口疾病谱的调查、医疗质量控制和医疗纠纷处置。
模式一:按照行政区划,分别设立中央级、省级和县市级法医中心,独立于公检法等司法部门,由各级政府直接监管,运行经费由各地财政预算划拨。专业管理由司法行政或卫生部门按照卫生或刑事技术系列统筹管理,业务活动按照现有模式与公检法部门衔接。现有的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和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分别确定为中央级法医司法鉴定北方中心和南方中心,作为国家级法医鉴定的统筹协调、研究和中央级层面的鉴定机构;各省法医中心作为省级法医司法鉴定统筹、疑难案件鉴定机构;县市级设立法医中心,作为日常法医鉴定机构,根据地区特点可以在偏远的县区设立派出机构。法医鉴定的人员和工作重心应置于县市级法医中心。管理方面可以参考现代公立医院管理模式建立现代法医中心管理制度。
模式二:在现有中央级的法医鉴定研究机构(如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基础上,司法行政部门和卫生部门联合各地高等院校共建法医学研究所/中心,作为各地的法医司法鉴定和研究平台,既可以保障法医司法鉴定的社会需要,也充分利用院校人才、技术优势作为法医人才的规范化培训和继续教育基地。法医鉴定费用采用政府购买模式,专业上列入卫生行业统筹管理,司法鉴定业务由司法部门按照法定规则监管。
为适应社会对法医鉴定日益增加的需求,鼓励条件较好的区域医疗中心设立法医科,开展法医病理、法医临床、司法精神病类鉴定。适度开放社会资本建立法医鉴定机构,并纳入公共卫生与健康、疾病与死亡管理体系。
五、结语
当前的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严重威胁人类健康、改变了人类和社会生态,随着人类活动的多元化扩张和生态环境的变化,未来各类病毒、微生物、食物和环境问题都可能不断威胁人类健康。后疫情时代,需要以“全健康”理念的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构建全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法医学科的发展不仅关乎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体验的公平和正义,也关乎国家公共卫生和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问题,法医学科的良好发展必须适合其特点、回归其应有的医学本位,以医学服务法治社会治理的集约化现代法医中心管理体系,推进法医学科更好的服务于公共卫生健康体系和国家法制建设,推进“健康中国2030”实施和“全健康”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