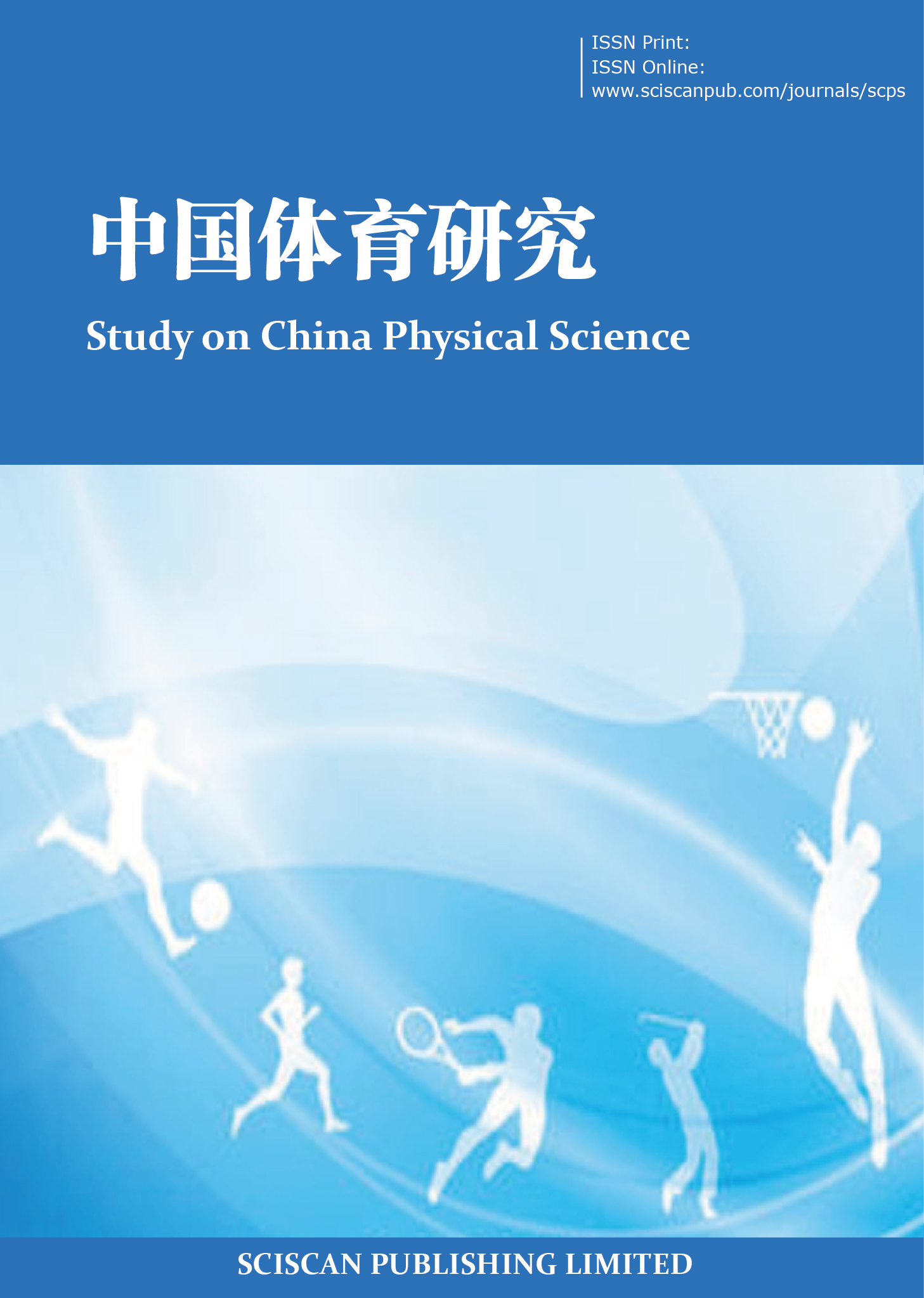Study on China Physical Science
刑法视阈下少数民族体育竞技行为正当化的思考——以蒙古摔跤为例
Thinking on the Justific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Sports Competitive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minal Law —Take Mongolian Wrestling as an Example
- Authors: 刘格
-
Information: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
-
Keywords:
Sports competition; Control theory; Social equivalence; Justification体育竞技; 控制理论; 社会相当性; 正当化
- Abstract: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for the injury or death caused in athletic games of the justification theory mainly includes the victim commitment theory, social equivalence theory and legitimate business theory, and so on. However, through analysis, it is easy to find that none of these theories can fully explain the damage caused by games. The control theory based on social equivalence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is problem. In addition, the scope of the justific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competition behavior is also limited. Specifically, it needs the qualification of the subject, the legitimacy of the purpose, the clarity of the rules and the completeness of the infrastructure. All conditions are indispensable. 我国学界对于体育竞技比赛中造成的伤害或者死亡的正当化理论主要包括被害人承诺说、社会相当性说以及正当业务说等。然而通过分析不难发现,这些学说都无法全面的解释比赛中造成的损害。以社会相当性为基础的控制理论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一难题。除此之外,少数民族比赛行为的正当化范围也是有限制的,具体而言需要主体的适格性、目的的合法性、规则明确性以及基础设施的齐备性,所有条件缺一不可。
- DOI: https://doi.org/10.35534/scps.0404022 (registering DOI)
- Cite: 刘格.刑法视阈下少数民族体育竞技行为正当化的思考——以蒙古摔跤为例[J].中国体育研究,2022,4(4):212-223.
1 问题的提出
体育竞技活动一般分为对抗型竞技和技巧型竞技,二者都有可能在比赛过程中发生人身伤害的情况,而前者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在2008年的奥运会上,中国球员谭望嵩为了发挥自身的防守优势,用脚攻击倒地的比利时球员波克尼奥利的下体,致使其双睾丸粉碎性撕脱,此事最终以谭望松的红牌处罚而告结。刑法学界对于体育竞技比赛中的伤害或者死亡关注较少,而少数民族体育竞技行为的探讨就更加寥寥无几。一般而言,对于体育竞技中出现的伤害情形基本上都不会追究刑事责任。究其原因,刑法理论上对于体育竞技正当化的法律依据缺乏深入的讨论,进而没有为其划定范围,才致使无论出现何种伤害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本文以少数民族体育竞技中的蒙古摔跤为例就其正当化的法律依据及范围展开分析,希冀能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帮助。
2 体育竞技行为正当化的法律根据
体育竞技行为的正当性依据在学界虽然尚未达成共识,但几乎都认为该行为的性质是正当的,对此“不言自明”。然而真相并非如此,实际上我们只有在法律上对于体育竞技行为正当化作出正面的回应,才可以在此基础上与其他的伤害行为区分开来。笔者将现阶段对于体育竞技行为正当性的依据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希望通过不同学说的比较分析找出最为合理的解释。
2.1 各种学说及其不足
2.1.1 被害人承诺说
该说认为,通过被害人或者权利人的承诺、同意就可以形成阻却违法性的事由,体育竞技就属于该种情况。正如意大利刑法典明文规定了“权利同意”为阻却违法事由。该法典的50条规定:“经可以有效地处置权利人的同意,对权利造成侵害或者使之面临危险的,不受处罚。”法国学者卡.斯特尼教授虽然对于被害人承诺是否完全阻却违法持保留态度,但是对于体育竞技中出现的人身伤害主张依据社会习惯,以被害人承诺理论将其责任予以消解。[1]除此之外,部分美国刑法学者也将此理论运用在体育竞技行为中,例如Sue Titus Reid教授就是提倡者之一。
笔者认为,被害人承诺对于体育竞技中行为的正当化解释并不全面,换言之,这一理论很难覆盖所有的体育竞技行为。例如,参加体育竞技的主体大多数是运动员,而对于运动员的界定并未区分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如此便产生出一个新的问题,即理论界和实务界都认为体育竞技中出现的伤害应该予以免责,但刑法理论上对于承诺的主体予以了严格的限定(未成年人不可进行承诺),二者出现了冲突。我国学者张明楷教授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被害人在承诺时,并不一定具备民法意义上的行为能力,只要对于对于被承诺的事项理解便可[2]。显然,此种观点意在对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进行化解,但是,这经不起推敲。一方面,如果将未成年的运动员在比赛中所造成的人身伤害正当化和常态化,那么它背离了刑法的目的——保障人权。具体而言,在竞技比赛中一个成年运动员对于未成年的造成伤害,二者的认知能力显然是存在差异大,如果无差别的将伤害统一正当化处理,无疑对于未成年运动员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体育竞技行为中的人身伤害包括致人死亡的情形,而这一点是刑法中被害人承诺理论所不能容忍的。所以,该理论存对于体育竞技行为中的伤害存在解释上的空白地带,无法适用。
2.1.2 正当业务说及其衍生的“区别对待说”
正当业务说认为,体育竞技既然是一种剧烈运动,那么设立之初就必然已经考虑到了可能的伤害,所以这些伤害无论程度如何都应该属于正当的业务。[3]正当业务说将理论解释的角度从国家转向了社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按照此理论所述,造成伤害的主体都严格限定在了专业运动员之间,将其他业余体育竞技参与者排除在外。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日本学者西田典之认为,实施拳击、摔跤、空手道等竞技体育活动之时,无论是职业选手还是业余爱好者,只要遵守了竞技规则,即便该当于暴行罪或者伤害罪的构成要件,也可以根据日本《刑法》第35条的规定阻却违法性[4]。之所以将这些行为予以正当化的理由在于,这些竞技活动除了能够增强健康并未国民提供业余娱乐生活之外,还同时符合被害人同意这一原则。
意大利学者帕多瓦尼认为,在正当业务的语境下,应该将体育竞技行为进行区别,分别讨论各自的性质。他指出,体育运动是一种法律允许的活动,对于期间造成的轻伤行为,如果没有超出《意大利民法典》第5条规定的范围,可以适用刑法典关于“权利人同意”的规定而不受处罚。但是,如果造成了肢体的残损(或死亡)就不能再适用上述规定。这时,造成上述结果的行为必须符合特定的条件、才是合法行为[5]。此种观点也被学者称之为“区别对待说”。
笔者认为区别对待说的优势在于通过二元制的分离方式做到了对损害特殊性的关切。具体而言,对于轻伤及其以下的伤害的法律效果通过被害人承诺理论来予以消解;然而对于轻伤以上的社会危害性则以行为人权利正当化来予以消除。此理论看似做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却存在致命的弱点。“区别对待说”是正当业务说的特殊形式,其都是以“权利”的行使作为核心要素而构建的理论“堡垒”,而这恰好也是症结所在。首先,任何部门法所强调的“权利”都是以法定形式出现的,而此理论对于伤害行为的辩护的“权利”确是一种理论上的,抑或在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产物,它无疑破坏了权利的基本特征——完整性(规范性)。其次,此种理论下,权利的内涵得到了极度的扩张,包括轻伤、重伤、甚至是死亡等。很显然,这是对于罪刑法定的挑战,退一步说,即便是相对罪刑法定的语境下,如此权利的行使也需要成文法的支持,否则便是类推思维流露。最后,此理论的最大特色在于从不同主体的角度对于伤害做正当化的解释。然而这种解释将轻伤以上的重伤害违法性的终结权交由行为人来决定,很显然违反了国民的自由意志,也使权利的行使秩序混乱不堪。
2.1.3 社会相当性说及合理风险说(被允许的危险说)
笔者之所以将社会相当性说与合理风险说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二者都是行为无价值语境下对体育竞技属于于违法阻却事由的探究。
社会相当性说认为,正当化义务的内容不宜肆意的扩张,而体育竞技行为是具有社会相当性的超法规阻却事由。体育竞技活动而进行的摔跤、拳击等活动,虽然不能说是业务,但是只要符合社会大众的道德观念,就应该定义为正当的[6]。社会相当性理论是以一般人为标准,判断该行为在日常生活中是否具有通常性的理论。但是,这种判断属于概括性的、多义性的、直觉的判断,根本无法成为明确的判断标准。例如,在蒙古摔跤的过程中,一方将另一方抱起摔倒在地,致使其背部重伤,此时的伤害行为是否能被社会大众所接受?显然,很难判定。社会相当性说无异于将体育竞技中法伤害性质的判断过程置于黑匣子之中,而仅仅发布结论。除此之外,在一定程度上,该说还留有纳入行为的反理论性等的余地。
合理风险说最早出现在《俄罗斯刑法典》中,成为其学界解释体育竞技行为正当化的理论源头。《俄罗斯刑法典》地41条规定,为了达到对社会有益目的而在正当风险的情况下,对受刑法保护的利益造成损害的,不构成犯罪。日本学界将此理论称之为“被允许的危险”,两种学说是在利益衡量的基础上所作出的价值选择。换言之,社会之所以会容忍这种风险的存在,是认为如果禁止该种行为对法益的损害远大于所保护的法益。笔者不否认该种理论具有一定的优势,其背后的价值理念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当出现了体育竞技过程中致人死亡的情形,该如何予以化解违法性?毕竟人的生命权要高于其他一切法益。
2.2 笔者的观点及理由
通过以上的论述,不难发现,现存的各种学说都存在理论或者实践中的瑕疵,难以为当前蓬勃发展的体育竞技提供智力支撑,所以应该摒弃或者重塑。笔者提倡以社会相当性为基础的行为控制说作为体育竞技中伤害行为性质的分析工具,进而结束“百家争鸣”之局面。此说的内容及理由如下。
2.2.1 “以社会相当性为基础的控制说”的内容
人作为高级的灵长类动物,自然避免不了侵略破坏的本性,例如,战争的发动、竞技体育就是例证。理想状态下,社会属性会战胜自然属性,但是由于社会与人之间的鸿沟存在,对本性的妥协就成为一种必然。蒙古摔跤作为一种少数民族运动,其中也难免带有人与人之间相互征服的色彩。社会承认并发展蒙古摔跤这种少数民族体育竞技,允许参与者在既定的规则范围内相互侵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顺应了人类的动物本性。申言之,这种体育竞技可能会造成参与者的伤害,但他却符合整体的社会大众观念,同时其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是有益的。基于此将社会相当性的理论作为蒙古摔跤阻却违法性的理论基础是合适的。但是问题在于上文中笔者也对于此种学说进行的剖析,发现其定义较为抽象,正是在理论上的兼容性,直接导致它在实践中却举步维艰的局面。故而,必须对其进行重塑。
有学者认为,应该将体育竞技中的正当行为独立出来,成为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所并列的违法阻却事由[7]。此种做法当然最理想的结果,但是实际上却很难对其予以理论化。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现存的违法组却事由目录表中,学界达成共识的已经有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法定的阻却事由和包括被害人承诺、义务冲突等超法规阻却事由。由此可见,违法阻却事由的大家庭成员数量已经足够庞大,其内部的讨论至今尚未停息,例如安乐死问题,所以如果盲目地将体育竞技行为独立成为新的类型,势必会加剧问题的复杂化。申言之,将体育竞技行为独立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至少目前是这样。
承接上文中提及对于社会正当性学说的改造进而使其能够为体育竞技行为的正当化提供理论依据。也有学者认为目前单一理论无法全面解释体育竞技中的伤害行为,于是提出了“一体双翼”理论,希冀破解目前困境。所谓“一体双翼”
也就是说,以被容许的危险理论为核心,以正当业务行为和被害人同意理论为两翼共同合理地构建竞技伤害行为的合法化根据[8]。此种理论似乎符合了我国学术界一贯的理论叠加现象,事实上对于问题本身的解决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因为容许危险理论、正当业务说以及被害人同意说之间时存在重合,将三种理论杂糅到一起,只会使原本的理论变得更加混乱不堪。
笔者认为将行为控制理论嵌入社会相当性中将会使概念明确化,结束各种学说分庭抗礼之局面。控制要件理论最早是由美国著名刑法学家道格拉斯·胡塞克(Douglas Husak)所提,其指出,该理论应该被视为描述和评价的综合体,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违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控制力的考量。控制要件应该成为行为要件的替代品,它能够将刑法和道德哲学融合在一起[9]。换言之,行为人如果对于某种事态缺乏控制,如果我们期待他或者她阻止这种事态的发生就缺乏合理性。
2.2.2 赞成的理由
社会相当性作为一种宏观层面上对于违法性的把握,涵盖内容较为广泛,这一特征使得其作为原则性的理论适用,但在具体问题判断上通常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是将其与控制理论结合在一起判断的根本原因。具体而言,社会相当性本质上是法律和道德对于人们行为的综合评价指标,这种指标具有普适性的特征,能够最大程度反映民意,且自身带有民族文化的标签。例如,对于为保护国家财产与抢劫犯搏斗的见义勇为之举,虽然造成他人的死亡,但社会相当性可以容许此种行为的发生,阻却违法性。但是对于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竞技单独依靠社会相当性理论却难以判断违法性,究其原因在于社会相当性的形成是整个国家文化、伦理以及道德等的折射,而文中所谈及的蒙古摔跤仅仅是民间体育运动,其背后蕴含的理念或者文化很难在整个社会达成共识。基于此,需要另一种理论来对这种判断机制予以限缩,为其所用。
既然是讨论违法性的判断,对于客观的行为的讨论在所难免。笔者之所以选取了控制要件来代替行为要件,关键在于该要件背后的核心旨意:任何人对那些他或她不能阻止发生或者获取的事态不应负责任。其为判断具体行为的正当化提供了清晰的逻辑思路。第一,判断行为人是否能够控制事态。很显然这属于禁言事实的问题。例如,在蒙古摔跤中,对于膝盖以下的违规接触属于可控制的。第二,无论行为人是否能够控制某一事态,存在“度”的问题。由于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够控制一种事态,存在一个“度”的区别规范性问题,所以在判断行为正当化时,必须判断行为人对某个事态究竟有多少控制。
3 体育竞技行为正当化范围的限定
刑法中的正当化是指行为客观上造成了他人的损害,但是不具有法益的侵害性,符合法律秩序的精神,所以不构成犯罪。本文中体育竞技行为的正当化顾名思义,特指在体育竞技过程中,虽然造成他人的伤害,但阻却违法性,因此是正当的。笔者认为在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时,体育竞技行为正当的。
3.1 体育竞技比赛目的具有合法性
体育竞技作为一种比赛,其目的必须是合法的。换言之,体育竞技比赛目的之合法性是正当化化的前提。以本文中的蒙古摔跤为例,虽然其看似规则简单(通常有一名德高望重的老者主持,不限时间,不分体重,膝盖以上的任何部位着地即为失败),但是其却历史悠久,且得到了国家的许可。2003年,国家体育总局把搏克运动与中国式摔跤融为一体,正式纳入全国摔跤锦标赛中。当然,如果未经允许,或者不遵守既存的比赛规则,私人之间进行摔跤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无疑是不具有正当性的。
可能有学者认为,体育竞技作为一种比赛,那就必须是经过国家或者有关体育组织所确认的比赛项目,且比赛必须是由体育机构或者正式组织的比赛[10]。笔者认为此种观点过于极端,其将比赛的目的予以了限缩解释,设置了诸多门槛,将会阻碍该项体育运动的发展。笔者认为比赛目合法性中的“法”应该是广义的法,包括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作为少数民族特有的体育竞技项目,蒙古摔跤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西汉初期开始盛行,元代广泛开展,至清代得到空前发展。由此可见,其发展是伴随着少数民族的历史而向前推进的,它不同于全国性或者全世界性的体育竞技项目有着同样的比赛准则。例如,足球比赛的规则FDC(国际足联纪律准则),基本上在全世界通用,并且有国际性的管理组织FIFA(国际足联),而蒙古摔跤是一种地方性的特色比赛,所以相对管理松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合法性缺失,相反,由于其传统性的特征使其合法性更加凸显。具体而言,只要蒙古摔跤的比赛符合既定的传统比赛习惯,能够被社会观念和伦理所接受,那么他就具有目的的合法性。例如按蒙古族传统要求,参赛选手上身穿牛皮或帆布制成的"卓得戈"(紧身半袖坎肩),裸臂盖背,“卓得戈”边沿镶有铜钉或银钉,这种服饰可能和其他的摔跤比赛有所不同,但作为一种少数民族文化,法律应当予以尊重和认可。事实也证明了,正是这些少数民族的特有文化传统才铸就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当然,这里有一点需要予以指明:文中提及蒙古摔跤为社会伦理所接受或者社会大众所接受,其也是相对而言的。毕竟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共融的大家庭,文化的差异性决定很难做到一种文化传统能被各民族都理解或者是接受,所以,笔者认为,只要蒙古摔跤这种体育竞技能被本民族和国家层面予以接受,那么此种行为就是正当的。
3.2 体育竞技比赛主体的适格性
既然摔跤也是体育竞技比赛的一种,主体与参与者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一般而言,体育竞技主体是运动员。为了提高节目的观赏性,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会面临着受伤或者死亡的危险,所以如果让摔跤手承受刑事责任则会影响这一民间赛事的发展。有学者认为裁判不参加比赛,所以不应该成为体育竞技的主体。换言之,裁判的适格性无关紧要。笔者对于此种观点不敢苟同。一方面,体育竞技比赛的进行需要裁判来主持,这一点对于都是成年人的选手来说意义可能较小,但是对于有未成年人参与的比赛项目,裁判的作用就极为关键。因为,未成年人对于比赛规则的理解有时存在偏差,需要现场的裁判在比赛过程中说明,蒙古摔跤便是例子。另一方面,对于具有民族特色的民间体育项目,裁判的适格性直接影响比赛的各个环节。由于克(蒙古摔跤的另一称呼)的民族特色性,比赛规则并不系统和全面,此时谙熟比赛习惯的主持人就变得特别重要。
比赛参与者是否都是职业运动员,理论上的争议从未停息。有学者认为职业运动员掌握专业的技巧,可以恰到好处的把握力度,所以其行为可以正当化,然而对于业余参与者未置可否[11]。笔者认为,对于类似于蒙古摔跤的民间体育竞技比赛选手可以是业余的。首先,搏克本身属于民间的体育竞技比赛,其之所以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也正是基于该民族特色。国家体育总局之所以将其纳入全国摔跤比赛中,目的是提高其知名度,而非对其进行改造。其次,业余体育活动时被社会观念所容忍的,应当阻却犯罪[12]。搏克作为蒙古族特有的比赛项目它不同于传统的职业比赛。传统的职业体育竞技更加注重利益,相较之而言,博克这种民间体育项目更加能够凸显体育的精神(以强生健体和娱乐为主要目的),既然前者能够为社会相当性所容忍,后者的正当化更应该得到承认。最后,按照洪福增教授的观点,如果单纯因为职业与否就将合法性做同等划分,则与国人的生活理念不相吻合。非职业的体育竞技包括传统比赛的主体非职业化和民间特有的体育竞技,二者都是长期以来人们生活方式的展现,不能因为法律规定之有无,就直接作出非职业体育竞技不合法的荒谬判断。
3.3 体育竞技比赛规则的明确性
无论是何种比赛,都离不开明确的规则,否则既不利于参赛者胜负的判定,也会使得观赏性大打折扣。任何正常的比赛规则都试图将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形都规定进去以求定纷止争,尽最大可能保护参与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博克是古老的比赛项目,所以其习惯也早已经被固定下来。具体而言,当裁判员发令后,参加者可以施展扑、拉、甩、绊等技巧以制胜。但是比赛严禁抱腿,不得搞危险动作,除脚掌外,其他膝盖以上的任何部位着地即为失败。与其他民族式摔跤不同的是,搏克比赛不受年龄和体重的限制,也无时间限制。至于这里的危险动作认定一般是由长者讨论决定。
当然即使违反比赛规制的行为无法使行为得以正当化,但并非都是犯罪行为。因为违法社会相当性的违规行为并不一定都是由刑法调整的,还要结合其社会危害性进行综合判断。
3.4 体育竞技比赛基础设施的齐备性
搏克既然属于一种体育竞技,就应该在基础设施具备的情况下,方可进行比赛。当然,一般情况下传统的体育竞技场地只要符合比赛要求即可,不需要其他的限制。然而,搏克,作为草原文化的象征,一般是在草原上举行。在比赛设施或者场地不符合蒙古摔跤的要求时,其造成的损害就不具有社会相当性。申言之,基础设施不具备的情形下所造成的伤亡是不具有阻却违法性的。所以,比赛的场地对于判断搏克比赛的正当性有一定的影响。
4 余论
蒙古摔跤作为我国现存为数不多的民间体育竞技比赛,如何在法律上保障其得以发扬和继承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然而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合理且合法的规范此种比赛行为,进而使得行为的正当化范围得以恰当圈定?笔者虽然对于该项运动的合法性依据以及正当化的范围做了讨论,但是对于可能出现的重伤或者死亡在刑法上应如何评价尚未作全面分析。
参考文献
[1] [法]卡·斯特法尼.法国刑法总论精义[M].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2] 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3] 马克昌.犯罪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821.
[4] 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M].王昭武、刘明祥,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69.
[5] [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刑法学原理[M].王昭武、陈忠林,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59.
[6] [日]大谷实.刑法总论[M].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93.
[7] 黄京平,陈鹏展.竞技行为正当化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6):27-36.
[8] 林亚刚,赵慧.竞技体育中伤害行为的刑法评价[J].政治与法律,2005(2):88-93.
[9] 孙国祥.刑法基本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00.
[10] 王政勋.正当行为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52.
[11] 张明楷.刑法学(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216.
[12] [日]野村稔.刑法总论[M].全理其,何力,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