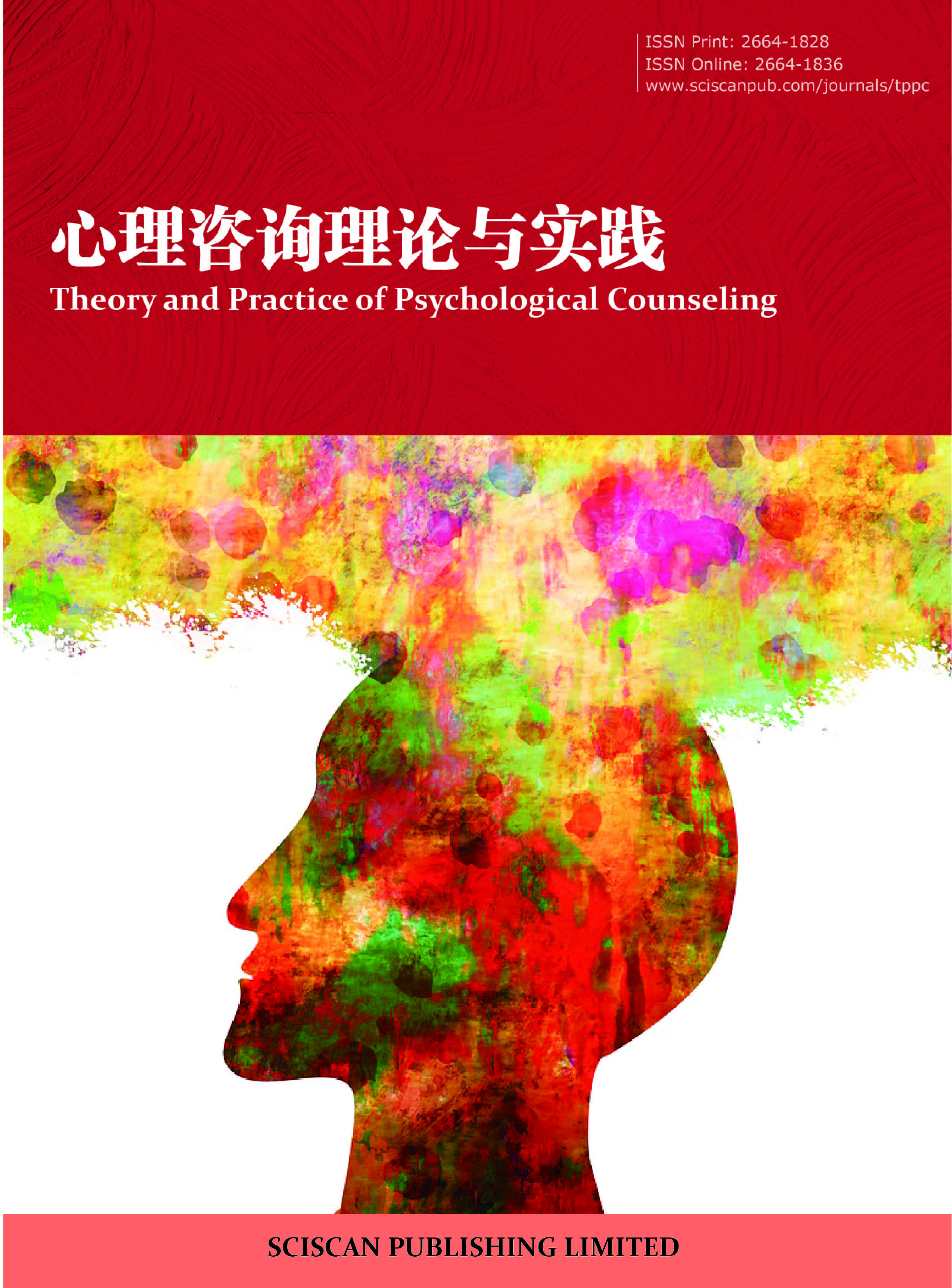Theory and Practice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沙盘游戏中巫婆意象的象征
The Symbol of Witch in Sandplay Therapy
- Authors: 黎映月
-
Information:
成都慧爱至臻心智发展中心,成都
-
Keywords:
Sandplay therapy; Witch image; Symbol; Archetype沙盘游戏; 巫婆意象; 象征; 原型
- Abstract: Based on Jung’s archetype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ymbolic meanings and clinical value of the Witch image in sandplay therapy. The study first analyz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ctive unconscious archetypes, pointing out that the Witch image is not a single negative symbol, but possesses multiple connotations such as “a spiritual wise person connecting heaven and earth” “a mother archetype with dual attributes of nurturing and devouring”, and “a mediator linking conscious and the unconscious”. Its symbolic direction changes dynamically with the client’s psychological state. Then, it explores the different symbolic meaning of the Witch image in the sandplay process through three cases. This study provides psychological counselors with specific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deeply understanding the inner world of clients and conducting personalized healing through symbols. 本文以荣格原型理论为依据,系统探究沙盘游戏中巫婆意象的象征意义与临床价值。研究先从集体无意识原型层面展开剖析,指出巫婆意象并非单一负面符号,而是兼具“沟通天地的灵性智者”“承载滋养与吞噬双重属性的母亲原型”“连接意识与无意识的中介者”等多元内涵,其象征意义随来访者心理状态动态变化。随后结合三个个案,详细分析巫婆意象在沙盘历程中的不同象征内涵。研究不仅丰富了沙盘游戏象征体系的理论内容,也为心理咨询师通过象征深入理解来访者内心世界、进行个性化疗愈提供了具体实践参考。
- DOI: https://doi.org/10.35534/tppc.0710082
- Cite: 黎映月. (2025). 沙盘游戏中巫婆意象的象征. 心理咨询理论与实践, 7(10), 749-757.
1 引言
沙盘游戏作为一种重要的心理治疗与分析技术,由多拉·卡尔夫创立。它借助沙、沙盘及丰富多样的沙具,让来访者在沙盘内自由创造意象场景,以此呈现内心世界。在沙盘游戏里,象征具有关键意义。沙盘中的意象所代表的象征含义,是连接来访者无意识与意识的桥梁。理解这些象征,就如同掌握了一把钥匙,能使咨询师深入理解来访者内心的情感、冲突与渴望,获得咨询思路和方向的线索,帮助来访者实现心理能量的转化与疗愈,这对沙盘游戏的实践与研究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
在临床工作中,巫婆的意象在来访者的沙盘游戏里常常出现。巫婆/女巫(witch)总是带着一种神秘感和魔力,在古代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常常出现在童话故事中。本文希望可以从原型层面来探讨巫婆在人类心灵中的重要意义,并通过案例来探讨巫婆象征对来访者的个人意义。
2 巫婆的原型意义
卡尔·荣格认为,个人无意识有赖于更深的层次的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是人类集体的共同的经验,具有普遍性,是超个人性的共同心理基础。集体无意识的内容是原型,原型无法直接被意识感知,只能通过象征,以意象的形式在意识中呈现(荣格,2011)。
因此,研究意象的原型象征意义至关重要,是理解这个意象对个人的心理意义的基础。
2.1 什么是巫婆
巫婆/女巫(本文中“巫婆”与“女巫”均对应英文“witch”,文化原型与神话场景中优先使用“女巫”,童话与沙盘个案场景中优先使用“巫婆”)指使用巫术、魔法等超自然力量的老妇人/女性,经常在民间传说和童话故事中出现。
汉字中的“巫”字,上下一横分别代表天与地,中间一竖是表示贯通天地,寓意沟通天地神灵的人。最初的巫师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是人与鬼神的媒介。他们可以预知未来,主持祈求神灵的祭祀、消灾灭祸的巫术、治疗疾病、占卜、送葬等事务,是最早的知识分子群体,也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在古代被视为先知先觉的人物。
很多研究倾向于认为,最早的巫师是在母系氏族社会中期出现的女巫。在《周礼》中有记载:“女性为巫,男性为觋。”巫女掌管礼法、祭典,能以舞降神、与神沟通,祭祀社稷山川。
2.2 不同文化中的巫婆
北欧神话传说中的渥尔娃女巫,是北欧异教中的萨满教女预言家,拥有很高的地位,甚至被认为拥有神之父的力量,能预测未来、为人祈福。埃及神话中,女神伊西斯因为拥有强大的法力,被尊称为女巫宗师(Chevalier & Gheerbrant,1996)。在希腊神话中,巫术女神赫卡忒是巫术与魔法的女神,可以教传授巫术与魔法的知识,为人指引道路(古斯塔夫,1959)。
直到今日,在非洲及太平洋岛国上有许多原始部落还有女巫的身影。她们或有超自然的通灵能力,或可以占卜,或可以用巫术治病,在各自的部落中往往都享有较高的声望,象征着内在的智慧、成长和疗愈(Ronnberg & Martin,2010)。
埃里希·诺伊曼认为,巫婆/女巫作为超自然力量形象的女性,是母亲原型的意象之一(诺伊曼,1998)。古老的斯拉夫女神芭芭雅嘎(Baba Yaga)是原型女巫,受到包括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等在内的各种斯拉夫民族的崇敬。在俄罗斯童话《美丽的瓦希丽莎》中,芭芭雅嘎的房子外围有一道篱笆,是用一排人骨头插着骷髅头做成的。任何靠近她的人都会被她吞噬。瓦希丽莎每天都遭受继母刁难,并且被继母派到芭芭雅嘎处取火。实际上继母希望她被芭芭雅嘎吃掉。然而瓦希丽莎在母亲留给她的娃娃的帮助下,完成了芭芭雅嘎交代的艰巨任务,芭芭雅嘎不仅允许她提问,还信守承诺赠予了她火种。
芭芭雅嘎充满了破坏、吞噬和毁灭的力量,同时也是个能提供帮助的智慧人物。她是较原始的母亲原型,同时是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混合了正向和负向/积极和消极两面,表现出大母神的二元面向。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体两面特质,蕴含着转化的可能。
荣格将女巫视为男性阿尼玛的投射,也就是男性无意识中的原始女性面向。女巫是负向阿尼玛的意象之一,拥有强大的能量,擅长引诱和诱惑、施行死亡巫术。对女性而言,则投射了自己的阴影在女巫身上,包括内心的欲望、恐惧和其他为意识自我不能接受的内容。可以说,女巫是理想化女性形象的对立面。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女巫的负面形象被认为是在基督教影响下的产物,是对古代女祭司、女预言家和女智者的蓄意歪曲。最初的女巫形象融合了有形和无形、人性和神性,被歪曲后的女巫穿着恶魔和丑陋的伪装,为魔鬼服务,和仙女是敌对的角色。在基督教的官方教义中,圣母玛丽亚仅保留纯洁高尚的积极面向,而消极面向,也就是被拒绝的阴影、邪恶恐怖的黑暗面向,则全部投射在了女巫身上。
这种投射在15世纪至17世纪的欧洲猎巫运动中达到了顶峰。在猎巫运动中,有大概10万女性被指控为女巫,遭到了残酷的审判和处决。这些被指控为女巫的一般都具有某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具有某种独特个性,或与一般女性略有差异,她们成了人们心理投射所认定为“女巫”而遭到迫害。
2.3 童话中的巫婆
在西方很多童话故事中,巫婆总是满脸皱纹、长着鹰钩鼻,戴着尖尖的帽子、穿着黑斗篷,骑着会飞的扫帚;或留着又尖又长的指甲,面露邪恶的表情;通常操控着水晶球、圆形大锅或魔镜,居住在森林最浓密的地方、隐秘阴暗的深谷或偏僻的小路。在《海的女儿》里,前往巫婆的住所,要穿越危险的漩涡、沼泽地和珊瑚虫森林,那里阴森恐怖,是海洋最黑暗最冰冷的地方,巫婆总是与边缘、神秘、恐怖的体验联系在一起(安徒生,2014)。
格林童话《汉塞尔和格莱特》中的巫婆,就是专门引诱孩子上当的邪恶形象。她用美食建造的房子,诱骗孩子们落入圈套,将他们煮来吃掉。这个故事中的“糖果屋巫婆”,呈现了大母神的负向特征——“诱陷”和“囚禁”。她以甜蜜的诱惑,以“喂养孩子”为借口,将他们养肥进而喂养自己。个体如果被引诱并沉浸在这样的“甜蜜”中,则会被她毁灭和吞噬。这个糖果屋对孩子来说就像天堂一样,象征着与母亲共生的状态,但如果停留在这样的状态中,个体独立的生命无法成长,甚至会危及个人的生存。
《莴苣姑娘》中的女巫,带走了刚出生的莴苣姑娘并将她养大,在她12岁时,将她关进了森林中的一座高塔。莴苣姑娘长成了世间最美的女孩,还有着美妙的歌声,却很寂寞,只有靠唱歌打发时间。女巫在隔绝外界污染和伤害的同时,将整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也隔绝掉了,所有其他的可能性也隔绝掉了。莴苣姑娘和现实世界脱节,活在自己构建的美好幻想世界里。这个女巫是原型自我照护系统的一部分。她既是保护者又是迫害者。其有利于生命的面向,她将莴苣姑娘照顾得很好,让其人格精神保存了下来;但同时,她也限制了心灵的成长。每当心灵有一丝希望或欲望的时候,她就会立刻予以打压。只有离开女巫的高塔、降落到大地上,也就是进入现实生活,脚踏实地过好每一天,自己养活自己、照顾自己,独立的人格精神才可能真正生长。
综上所述,巫婆/女巫沟通天地神灵,和内在的智慧、成长和疗愈有关,可以是一个较原始的母亲原型,兼具正向和负向、积极和消极两面,表现出大母神的二元面向;也可能是毁灭和吞噬的象征,是被拒绝的阴影,代表着邪恶恐怖的女性黑暗面向;既可以是能提供帮助的智慧人物,也可能既是保护者,又是迫害者。
3 沙盘游戏个案中的巫婆
接下来本研究将呈现三个个案,结合他们的沙盘游戏过程,讨论巫婆的象征意义。
3.1 个案1:男,8岁
小杰是一名小学三年级的男孩,生活在孤儿院,有较高的焦虑情绪。他的手总是停不下来,注意力不集中,有时上课睡觉,有时扰乱课堂秩序。
小杰的母亲在生下他20多天后就离家,并且再也没有出现过。他最初由大姑和祖父母照顾,父亲在他1岁时因为酒精中毒去世。4岁时,小杰由大姑带到孤儿院,家人没有主动来接他回家。小杰生命早期的家庭变故和成长经历,给他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创伤。被母亲抛弃、被大姑送到孤儿院的经历,激活了他母亲原型的消极面向,进而形成了以恐惧和不安为核心的消极母亲情结,他外在焦虑的呈现,都和他内心深处的恐惧和不安有关。
幸运的是,在孤儿院的集体生活中,他是年龄最小也是最受“妈妈”(即他所在带养单元的工作人员,此个案下文提到的“妈妈”均指该工作人员)喜爱的孩子。同一“妈妈”带养的还有两位比小杰大的女孩,他称呼她们为姐姐,共同生活在同一栋房子里。
本次沙盘(如图1所示)是在第10次咨询中做的。小杰说今天“妈妈”出门了,姐姐跟他说12点之前回家吃饭,结果他在外面玩耍到12点半才回去,不仅没有吃到饭,还被姐姐批评,说他没有听“妈妈”的话。可见,姐姐在家里某种程度上也承担了“妈妈”的角色,尤其“妈妈”不在场时,而且是比较严苛的“妈妈”的形象。

图 1 个案1的第10次沙盘
Figure 1 The 10th sandplay of case 1
小杰先放了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沙具在沙盘里,然后放了城堡在公主后面,接着放入石头和巫婆,最后放入卫兵和栅栏,研究者在沙盘的左侧。
小杰对沙盘的讲述是:“白雪公主在跟小矮人告别,她要回到皇宫去了,不能一直待在外面。有两个巫婆躲在石头后面想要伤害白雪公主,因为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她们想把她的脸换到自己的脸上。但是因为这里有守卫,而且大门打不开,她们进不来,就逃走了。守卫们趴在地上是为了隐蔽,不让巫婆发现,如果巫婆过来就抓住她们;巫婆走了之后,他们就不需要隐蔽了,就重新站起来了。”
小杰和严苛的姐姐相处时的经历,激活了他内在母亲原型的消极面向,这个面向在沙盘中以巫婆的意象呈现。而巫婆想换取白雪公主的容貌,也体现了嫉妒的主题。姐姐可能嫉妒他受到“妈妈”的宠爱,他可能嫉妒姐姐比他有更大的话语和支配权力。
3.2 个案2:女,16岁
白雪是一名16岁的高二女生,因为考试没考好出现情绪崩溃,进而前来咨询。来访时,白雪有较高的焦虑情绪,在学校上课时常常走神,反复担心别人对她的评价,总是不断回想审视自己的行为,注意力不能集中、入睡困难,导致学习效率下降和成绩下滑。
白雪出生在西南地区的一座城市,父亲经营面馆,母亲没有外出工作,负责在家照顾并教育白雪。白雪没有上过幼儿园,由母亲在家教她幼儿园的课程。小学时也由母亲辅导她的作业。如果她犯错,会受到母亲严厉的惩罚,如罚抄、打手心或在楼道罚站。因此,她从小就表现得非常听话,母亲会借白雪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而白雪会配合母亲。
在白雪的成长过程中,她总是被要求按照外部标准表现自己,符合他人的期待。她和内在严苛、忽略自我的消极母亲意象融合,一旦没有满足这份内在母亲的期待,她就会陷入恐惧与不安,呈现出以上的焦虑表现。她习惯性地忽略自己的真实感受,个体生命的自主性也无法得到发展。
白雪正处于青春期阶段。埃里克·埃里克森认为,青春期的主要任务是应对同一性与同一性混乱的危机,以便将来成为一个独一无二、有着一致自我认识,并能在社会上发挥自己价值的个体。“在本阶段所要达到的整体,我便称之为内部同一感。”(埃里克森,2015)白雪在这个发展阶段的议题,正是要培育自己的个体生命自主性,而只有和内在的消极母亲意象分离,她才能发展出自己的个体生命。
本次沙盘(如图2所示)制作前,在咨询中谈到白雪的祖母。祖母在世时,是白雪最信任的人,会给她准备各种好吃的食物,帮她驱赶虫子,思想很新潮(这是具有保护、养育的积极母亲意象)。一年前,祖母因病去世,白雪当时几近崩溃,每晚在房间里偷偷哭。

图2 个案2的第1次沙盘
Figure 2 The 1st sandplay of case 2
这是白雪的第1次沙盘创作,在第18次咨询中进行。研究者在沙盘的右侧,白雪在放完左上角和右上角的其他沙具后,放了中间的彩虹,然后是这个巫婆和救护车后面的病人沙具。
和通常的女巫形象不同,这个沙盘中的巫婆(如图3所示)是一位和蔼的老奶奶,在开心地笑,她戴着女巫帽,怀里抱着老鼠(老鼠常常和巫婆形象有关)、脚下有一盏南瓜灯,慈祥的面容就像邻居家的老奶奶。

图 3 个案2沙盘中的巫婆
Figure 3 The witch in the sandplay of case 2
白雪对沙盘的讲述是:“彩虹是屏障,隔开沙盘的两边,中间是海,左边是神秘,右边是现实,中间的桥可以通行。巫婆很厉害,会很多巫术,但有点小家子气,对欺负她的人,她会捉弄或报复;对喜欢的人或帮她的人,她会回报以惊喜。我喜欢这个巫婆,想跟她成为朋友。”
很显然,这个巫婆带有芭芭雅嘎原型女巫的属性,亦正亦邪,还带有一些人性温度,更偏向于母亲原型的积极面向。巫婆旁边是贝斯特猫沙具,有着母亲原型的积极面向象征意义。左边的是葬送女神塞尔凯特,她是医术女神,擅长治愈毒虫咬,是死者的保护神;右边的是索普度,职责是保卫埃及东部边界,打击侵犯者。这两位神都和“保护”有关,塞尔凯特还有疗愈的象征内涵。
白雪在这一节谈到祖母的死,以及祖母生前对她的保护和养育。这个和蔼的巫婆的形象,可能和祖母在她生命中流下的积极母亲经验有关,这些经验激活了她内在母亲原型的积极面向。这个巫婆意象的出现,可能表明聚集在白雪内在消极母亲意象上的能量开始松动,正在向积极的母亲意象流动。她正在从母子一体阶段的创伤中逐步疗愈,和内在的消极母亲意象分离,发展属于她自己的个体生命。
3.3 个案3:女,27岁
小兔是一位27岁的女性,2年前确诊为中度抑郁,目前仍在持续服药。她的前领导非常严格,对她总是批评、指责与压榨。她很难受,但始终没有表达,一直支撑到项目完成,被确诊抑郁。
小兔从小被送到祖母家养育,直到上小学时回到父母身边。祖母很严厉,小时候她尿床时,会半夜被拎起来打。小兔认为自己从小一直很乖很听话,讨好父母,但父母不理解她。她常常陷入自我怀疑,总是因为别人的某句话或某个表情,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就算知道不是自己的错,但还是忍不住在内心责怪自己,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经过一段时间的咨询,小兔开始意识到,批评指责她的不是别人,正是她自己,是自己内化的那个批评的声音,一直在指责和“鞭打”着自己。
小兔先放了丧尸和小丸子在沙盘中,丧尸在左下角,小丸子在沙盘中间的小沙堆上,接着她放了巫婆、大力士和尖帽子的小孩(如图4所示),研究者在沙盘的右下角。

图 4 个案3的第1次沙盘
Figure 4 The 1st sandplay of case 3
小兔对沙盘的讲述是:“丧尸(如图5所示)就是我内在那个总是批评的声音,我想让这个丧尸去死,再也不要出现了。小丸子是另一个自己,被批评的我很可怜。”她说:“其他几个人和我一起对付丧尸。巫婆会黑魔法,这个男人有力量,这个(戴尖帽子的)小孩虽然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但看着他就很安心,他可以陪伴我。”

图 5 个案3沙盘中的丧尸
Figure 5 The zombie in the sandplay of case 3
这个巫婆沙具(如图6所示)戴着紫色的尖帽子,穿着黑色的裙子,拿着扫把,长着尖尖的鹰钩鼻,神秘又透着点邪气,是典型的传统巫婆形象。在小兔的讲述中,这个巫婆会黑魔法,魔法是有转化的功能的,也就是“巫”的特征的表现。因此,这里会黑魔法的巫婆,可能是一种“转化”的象征。

图 6 个案3沙盘中的巫婆
Figure 6 The witch in the sandplay of case 3
正如茹思·阿曼所指出的,当无意识的心理内容在沙盘中以意象的形式呈现,被看见后,这些内容所承载的能量就可能开始流动(Ammann,2012)。讲述完沙盘之后,看了沙盘一会儿,说:“他(丧尸)可能也没那么恐怖那么坏,只是不健全。”当小兔的消极母亲情结聚集的意象——丧尸和小丸子,迫害者和被迫害者——一起出现在沙盘里,同时,有着转化象征的巫婆意象也出现在沙盘里,出现在同一个空间和容器中被看到,于是她内在聚集在消极母亲情结上的能量开始流动,丛集在丧尸身上的恐惧减轻了。
4 结论
综上,巫婆意象在沙盘游戏中具有丰富且多元的象征意义,既承载着原型层面的复杂内涵,又反映着来访者的个人心理状态。不论是掌管世界的芭芭雅嘎,还是童话故事中常见的“邪恶继母”、恶毒邻居,或转化的“捣蛋鬼”,巫婆意象在童话故事中及来访者的沙盘游戏历程中,始终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深入探究该意象的象征内涵,能为咨询师搭建理解来访者内心世界的桥梁,推动心理疗愈进程,也为沙盘游戏中象征意义的研究增添了重要的实践依据,对相关领域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本研究仅基于3个个案展开分析,存在一定局限性:样本量较小,且个案均来自单一文化背景,结论的普遍性有待进一步验证。未来可扩大样本量,纳入跨文化背景个案,探究不同文化背景下来访者对巫婆意象的象征理解差异,或结合纵向追踪研究,观察巫婆意象在长期咨询的沙盘游戏历程中的动态变化,及其与个案人格发展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荣格. (2011). 原型与集体无意识 (徐德林 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 Chevalier, J., & Gheerbrant, A. (1996). 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Symbols. London: Penguin Books.
[3] Ronnberg, A., & Martin, K. (2010). The book of symbols. Cologne: TASCHEN Gmbh.
[4] 古斯塔夫. (1959). 希腊神话和传说 (楚图南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5] 安徒生. (2014). 安徒生童话全集 (叶君健 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6] 诺伊曼. (1998). 大母神 (李以洪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7] Ammann, R. (2012). 沙盘游戏中的治愈与转化:创造过程的呈现 (张敏 等译).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8] 埃里克森, E.(2015). 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 (孙名之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