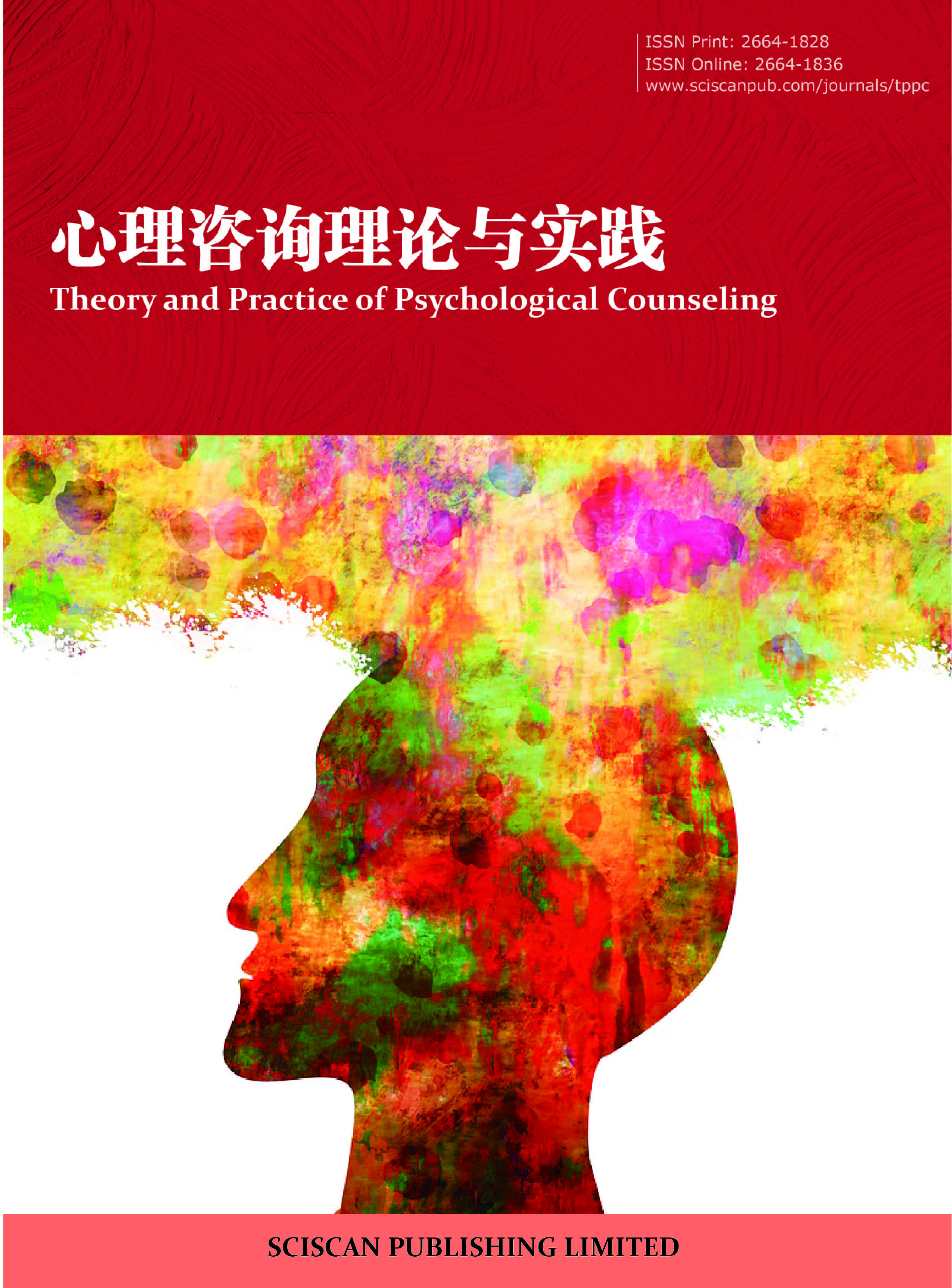Theory and Practice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无为”之有为:心理咨询实践中“知常”智慧的实践与理论初探
Action in “Non-Action”: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Knowing the Constant” Wisdom in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 Authors: 龚琳轩
-
Information:
移空技术研究院,西安
-
Keywords:
Non-action (Wu Wei); Knowing the constant (Zhi Chang);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Selfcultivation; Localization; Practical wisdom无为; 知常; 心理咨询; 自我修炼; 本土化; 实践智慧
- Abstract: Based on the author’s nearly two decades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practice and eight years of systematic cultivation grounded in traditional practic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interpret and reconstruct the practical value of the concepts of “non-action” (Wu Wei) and “knowing the constant” (Zhi Chang) from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modern psychology. The author posits that the professional efficacy of a counselor depends not only on technical proficiency but is more deeply rooted in their profound recognition of and respect for the natural rhythm of life (“the constant”). This paper makes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non-action” and “inaction”, as well as between “impulsive intervention against the natural rhythm of life” (Wang Zuo) and “conscious action” (You Wei), highlighting their essential differences. It further proposes that “knowing the constant” is the core competency enabling counselors to navigate the creative pendulum swing between intervention and accompaniment. Drawing on clinical cases, the article elucidates the path to achieving “knowing the Constant” through selfcultivation. The aim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developing a more culturally adaptive, profound, and effective localized model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本文基于研究者近二十年的心理咨询实践与近八年的系统性传统修炼体悟,试图在现代心理学框架内,重新阐释与构建我国传统文化中“无为”与“知常”思想的实践价值。本研究认为,咨询师的专业效能不仅取决于技术精熟度,更深植于其对生命自然节律(“常”)的深刻体认与尊重。本文首次明确区分了“无为”与“不作为”“妄作”与“有为”的本质差异,并提出“知常”是咨询师在干预与陪伴之间实现创造性摆荡的核心能力。文章结合临床案例,阐述了通过自我修炼达成“知常”的路径,旨在为构建更具文化适应性、更深邃有效的本土化心理咨询模式,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探索。
- DOI: https://doi.org/10.35534/tppc.0711093
- Cite: 龚琳轩. (2025). “无为”之有为:心理咨询实践中“知常”智慧的实践与理论初探. 心理咨询理论与实践, 7(11), 846-852.
1 引言:被误解的“无为”与咨询师的实践困境
在当代心理咨询实践中,咨询师的“主动性”与“被动性”之间存在普遍张力。受西方主流“问题解决”导向临床培训模式的影响,许多从业者更习惯于通过结构化干预体现专业价值。包括早期的研究者在内,常陷入一种“干预焦虑”(Intervention Anxiety)——即担忧若不能在咨询中展现出明确、结构化的“作为”,便无法证明自身价值,甚至可能辜负来访者的期望。这种焦虑的深层根源,在于将“行动”(Action)等同于“效能”(Effectiveness),而将“静止”(Stillness)或“空间保持”(Space-holding)误读为“专业能力的缺失”(贺琳,2025;凯恩,2012)。
这种困境在心理咨询培训体系中尤为明显。新手咨询师往往被教导要“做些什么”——运用特定技术、提供解释与给予建议,似乎只有通过可见的“行动”才能体现专业性。然而,这种强调“有为”的倾向,可能导致咨询师忽视了倾听的艺术、沉默与留白的力量及陪伴本身所具有的治疗价值。更为严重的是,当咨询师过度依赖技术性干预时,可能会无意识地阻碍来访者内在智慧的自然呈现,干扰其自我疗愈的过程及心理功能的发展和完善。
本研究在回归我国传统文化智慧中寻求解答时发现,《老子》中“无为而无不为”与“知常明也。不知常,妄。妄作,凶。”的论述(张松辉,2024),提供了超越二元对立的视角。西方心理学中,人本主义的“非指导原则”、正念疗法的“接纳态度”,与“无为”思想存在相通之处,二者可形成互补。罗杰斯(Carl Rogers)提出的“无条件积极关注”和“共情理解”(罗杰斯,2013),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无为”的精神——通过创造安全、接纳的环境,促使来访者自发地朝着成长和自我实现的方向发展。同样,正念减压疗法(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MBSR)、接纳与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ACT)中强调的“不评判的觉察”(史蒂文,杰森,2020),也与“无为”思想中的“不妄作”理念相呼应。
然而,“无为”在心理学语境下常被简单理解为“不做任何事”,使其丰富内涵被严重扁平化。这种误解不仅存在于西方心理学界,即使在我国的心理咨询实践中,“无为”的深刻内涵也往往被忽视或简化。本文旨在厘清这些核心概念,并基于研究者的亲身实践,系统论述“知常”如何成为咨询师专业素养的基石,以及“无为”如何作为一种积极、生成性的治疗姿态深刻影响咨询进程。
2 理论构建:厘清“知常”与“无为”“有为”
2.1 “知常”:咨询实践的元能力
“常”,意指宇宙与生命本然、固有的运行规律与秩序。在《老子》中,“常”被视为道的基本属性。“知常明也。不知常,妄。妄作,凶。”这一概念不仅具有哲学意义,在心理咨询的语境下更具有深刻的实践价值。“知常”意味着咨询师对人性发展、情绪流动、关系互动及疗愈发生的内在规律,拥有一种超越理论知识、体验式的深刻理解与坚信。
从更深层次来看,“知常”包含三个维度:首先是知“生命之常”,即理解生命本身具有自我调节、自我修复的内在倾向;其次是知“情绪之常”,即认识到情绪如自然现象相似,有其发生、发展、高潮、消退的自然过程;最后是知“关系之常”,即明了真诚、尊重、共情的关系本身具有治疗作用。这种知“不”是简单的认知理解,而是通过长期实践和内省获得的体认,它使得咨询师能在复杂多变的咨询情境中保持内在的稳定和方向感。
“知常”的咨询师,其内在是安稳与清明的。其不再试图扮演“生命的修理匠”,而是成为“生命过程的守护者与见证人”。这种状态的最高境界,在《帛书老子》第四十三章中有精妙的描绘:“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出于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能及之矣。”(张松辉,2024)
这段论述为理解“无为”的临床效能提供了经典的哲学依据。“至柔”的“无为”状态,何以能驰骋贯穿于“至坚”的心理防御与固着模式?正因其“出于无有,入于无间”——它源于一种不带有个人意志强加、虚静的状态(无有),故而能够无孔不入地(入于无间)贴近来访者最真实的内在体验。咨询师能最终在“有为”与“无为”之间出入自由,正是因为他通过亲身修炼,体验和体认到了这种“无为之益”,见证了“不言之教”所带来的深刻改变。这种体认,超越了理论上的认同,成为一种内在的确信,即最有效的干预有时恰恰源于不干预、纯净的“在场”(海因茨,1981)。
2.2 “无为”与“妄作”:基于“知常”的判别
在“知常”的基础上,可以清晰地界定“无为”与“妄作”。这一区分对于心理咨询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帮助咨询师在复杂多变的临床情境中做出恰当的专业判断。
2.2.1 无为
无为并非消极的“不作为”,而是指咨询师在深刻体认生命自然节律的前提下,自然放下了不必要、源于自身焦虑的干预冲动,为来访者的内在智慧浮现创造充分的心理空间。它是一种高阶、充满信任的“在场”(Presence)(Geller & Greenberg,2012;Geller et al.,2010;Geller & Porges,2014)。
从操作层面看,“无为”在心理咨询中体现为多种形式:首先是“语言的无为”,即在适当的时刻选择保持沉默,让来访者有空间消化体验、连接内在智慧;其次是“技术的无为”,即不被技术所束缚,而是根据当下情境灵活选择是否使用技术;最后是“目标的无为”,即不执着于预设的治疗目标,而是尊重来访者自身的发展节奏和方向。这种“无为”本质上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反应,它建立在咨询师对进程深度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
2.2.2 妄作
妄作则特指在“不知常”状态下,咨询师基于自身(而非来访者)的需求——如对控制感的渴求、对“完美咨询”的幻想、对自身无能的恐惧——而进行违背生命自然规律的强制性干预。最常见的“妄作”,即与来访者共谋,追求“彻底消除负面情绪”或“达到永恒快乐”等脱离生命常态的幻觉性目标。
在临床实践中,“妄作”可能表现为多种形式:过早的解释、强行的面质、过度频繁的技术介入、超出来访者承受范围的深度探索等。这些“妄作”表面上看起来是咨询师的“积极作为”,实际上却可能阻碍自然的疗愈进程,甚至对来访者造成二次伤害。“妄作”的根源在于咨询师自身的不安全感和对自然过程缺乏信任。
2.3 “有为”的恰当位置:在“无为”的土壤中生发
强调“无为”的价值,并非否定一切“有为”的干预,而是要为其确立根基与方向。“无为”并非“有为”的对立面,而是“有为”得以真正有效的底色与前提。真正的“无为”为有效的“有为”提供了孕育的土壤、清晰的边界与不竭的源头。当咨询师通过自我修炼而“知常”,他的内在便拥有了这份“无为”的底色——一种清明的觉察与稳定的临在。在此基础上,他的任何“有为”之举——无论是运用认知重构、情绪聚焦还是诠释技术——都将从这份底色中生发,从而呈现出精准、适时、与来访者当下的生命节律同频的特质。这样的“有为”完全服务于来访者内在的成长进程,而非咨询师个人的议程。它不再是生硬的技术操作,而是“无为”精神在行动层面的自然延伸,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整体。至此,心理咨询将升华为真正的“生命关怀”,而非仅是“技术关怀”。
在咨询过程中,“有为”与“无为”依据进程节律形成动态平衡,而“无为”的底色始终贯穿其间。例如,在建立关系的初期,可能需要更多“有为”设置框架,但此“有为”的背后,是“无为”的倾听与不评判的接纳作为底色;当信任关系建立后,咨询师可以更多的“无为”陪伴,支持来访者的自我探索;当进程遇到阻碍时,又需要适当的“有为”突破困境。这种灵活的切换能力,正是“知常”咨询师的专业体现,但“无为”始终是“有为”的底色。
3 方法论:达成“知常”的自我修炼路径
“知常”作为一种体验性的能力,无法仅通过阅读和思考获得,必须通过持续、系统的自我修炼(Self-Cultivation)来内化。本研究的路径主要依赖于以打坐为核心的传统内观实践。这一路径的选择基于两个重要认识:第一,咨询师自身的状态是咨询过程中最重要的“工具”;第二,只有通过深度的自我体认,才能真正理解生命的运作规律。
3.1 修炼作为“体验实验室”
每日的打坐,是研究者个人的“心理学实验室”。在此过程中,并非追求神秘体验,而是以自身的身心为观察对象,体证“心念活动”(意动、神动)如何影响“呼吸”(气),进而影响整个身体的紧张与松弛状态(精)。例如,一个焦虑的念头会立即引发呼吸浅促与肩颈紧绷;而当有意识地放松身体、回归呼吸时,纷乱的思绪也会自然平息。这种第一手、反复验证的身心体验,让研究者对“身心一体”“气随神动”等传统智慧建立了不可动摇的“体认”(Embodied Understanding)。这份体认,是咨询中保持深度共情而不迷失、稳定包容而不疏离的内在基石(瓦雷拉 等,2010)。
这种自我修炼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觉察阶段”,通过静坐培养“不卷入之心”——“观察者的稳定性”,在此基础上发展对身心现象的敏锐觉察力;第二是“理解阶段”,在觉察的基础上,开始理解身心现象的相互关联和变化规律;第三是“体认阶段”,在持续实践中将这些理解内化为无需思考的自然反应。整个过程类似于学习骑自行车——从有意识的努力到无意识的熟练,最终达到“行知合一”的状态。
3.2 修炼塑造咨询姿态
这种修炼直接塑造了研究者的咨询姿态。在打坐中,核心练习是“不拒不迎”:对产生的念头和情绪,不抗拒其存在,不追逐其延续。这一练习直接迁移到咨询中,成为面对来访者任何想法、感受与行为时的核心态度——深度接纳。咨询师内在的这份“不评判的宁静”,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疗愈场,向来访者示范并传递着与自身经验和睦相处的可能性。
具体而言,这种修炼带来的改变体现在三个层面:在认知层面,咨询师能更好地区分“事实”和“对实事的解释”,避免将自己的理解强加给来访者;在情绪层面,咨询师能保持情绪的稳定,不被来访者的情绪风暴所卷入;在行为层面,咨询师能更好地把握干预的时机和程度,避免过度或不足的介入。这些能力的提升,都源于修炼带来的不卷入之心(自持力)、自我觉察和自我调节能力的增强。
4 临床实践:从“知常”到“自在”的咨询艺术
当咨询师初步“知常”,其咨询实践将发生质变。这种变化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整个咨询姿态和范式的转变,以下通过具体案例来说明这种转变在实际工作中的体现。
4.1 从“挖掘问题”到“创造空间”
本研究不再将来访者视为一个需要被“剖析”和“修复”的问题集合体,相反,致力于“创造一种安全的、允许无预设目标的自由对话空间”。当咨询师放下“专家”的挖掘姿态,来访者的防御会自然降低,其真实的核心困扰会自发地“呈现”(Presentation)而非被“逼问”(Extraction)出来(贺琳,2025;罗杰斯,2013)。
例如,一位长期受困于人际敏感的来访者,在传统的咨询框架中总是试图“分析”自己为何如此敏感,结果陷入了更深层次的自我批判。当咨询师转而采用“创造空间”的姿态,简单地邀请:“也许我们可以不急着改变敏感这个特点,而是先好奇地了解一下,这个敏感是如何在你身体里运作的?”这一微妙的转变,使来访者从“问题的拥有者”变成了“自身经验的探索者”,咨询氛围从评判转向了好奇,深刻的转变由此自然发生。
在这个案例中,咨询师的角色从“问题的解决者”转变为“探索过程的陪伴者”。这种转变的核心在于信任——信任来访者内在的智慧,信任自然展开的过程,也信任咨询关系本身的力量。当咨询师放下“必须有所作”的压力,反而为更深层的改变创造了条件。
4.2 在“干预”与“陪伴”间自如摆荡
本研究能够更敏锐地感知咨询进程的“节律”。在来访者内在探索动力充沛时,选择“无为”的跟随与见证;当其陷入固着模式或需要新的视角时,则以“有为”的方式进行澄清、面质或提供框架。这种摆荡是流畅、响应性的,而非机械的技术切换。
以一位经历哀伤处理的来访者为例:在其泪流满面地诉说时,咨询师选择保持深沉的“无为”陪伴——不急于安抚,不打断情绪的流淌。然而,当来访者陷入“如果当初我……”的强迫性思维反刍时,咨询师则会温和而坚定地进行“有为”的干预:“我注意到你又一次开始责备过去的自己,我们是否可以暂停一下,先感受此刻心里的滋味,并把你感受到的告诉我?”这种基于深度共情的干预,往往能帮助来访者从思维的漩涡中回到当下的体验。
这种自如的能力建立在咨询师对进程的敏锐觉察基础上,它要求咨询师既能够深入参与,又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进行观察;既能够共情来访者的体验,又能够看到超越当下体验的可能性。这种能力的培养需要时间和实践,但其核心在于咨询师自身认知的稳定和清晰。
4.3 确立稳固的专业定力
“知常”意味着清晰地知晓咨询师能力的边界。研究者能够平和地向来访者及其家属阐明:本职工作是提供专业的陪伴与引导,而改变的最终责任与节奏,在于生命本身。这种基于现实的真诚,反而建立了更健康的咨访关系,并有效防止了咨询师的职业耗竭。
在实践中,这种专业定力体现在多个方面:第一是在设置维护上的坚定,能够清晰而温和地保持咨询框架;第二是在期望管理上的诚实,能够帮助来访者建立合理的咨询期望;第三是在责任划分上的清晰,能够明确咨询师和来访者各自的责任范围。这些看似简单的专业行为,实际上都源于咨询师内在的稳定和清晰。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论述了,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无为”与“知常”思想系统性地融入心理咨询师的专业认同与日常实践,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它指引研究者超越对“技术万能”的迷信,回归对“生命本身”的敬畏与信任。
咨询师的核心能力,最终将是通过持续自我修炼而达到的“知常、明达、安稳、自在”的生命状态。未来的本土化心理咨询研究,应更加重视咨询师的内在修炼体系构建与实证,探索如何将传统智慧与现代心理学知识相结合,具体而言,可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探索:首先,建立系统的咨询师自我修炼课程体系,将传统的修炼方法与现代心理学理论相结合,形成既有深度又具有操作性的训练方案。这个体系应包括不同阶段的修炼目标、具体的方法指导及效果评估标准;其次,应该开展相关的实证研究,通过科学方法验证自我修炼对咨询师专业能力和咨询效果的影响。这类研究可以采用混合研究方法,结合量化数据质性分析,全面评估修炼对咨询实践的影响;再次,需要探索将“无为”和“知常”的理念整合至咨询师督导体系。传统的督导侧重于技术指导和案例概念化,如果能融入基于“知常”的督导理念,可能会对咨询师的成长产生更深远的影响;最后,应该加强跨文化对话,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与西方心理咨询理论进行更深层次的整合。这种整合不是简单的理论拼凑,而是在实践基础上的创造性融合,可能会催生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方法。
培养出不仅“会做”而且“懂得不做”、能与来访者生命本质深度共鸣的新一代心理咨询师,是本土化心理咨询发展的重要方向。希望这篇文章能够为行业同仁提供新的思考维度,引发更多关于心理咨询本质的深入探讨,共同推动具有我国文化特色的心理咨询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1] 贺琳·安德森. (2025). 合作取向治疗:对话·语言·可能性.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2] 凯恩, S. (2012). 安静:内向性格的竞争力. 北京: 中信出版社.
[3] Geller, S. M., & Greenberg, L. S. (2012). Therapeutic presence: A mindful approach to effective therap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4] Geller, S. M., Greenberg, L. S., & Watson, J. C. (2010). Therapist and client perceptions of therapeutic presence: The development of a measure. Psychotherapy Research, 20(5), 599-610.
[5] Geller, S. M., & Porges, S. W. (2014). Therapeutic presence: Neuro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mediating feeling safe in therapeutic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Integration, 24(3), 178-192.
[6] 史蒂文·C. 海斯, 杰森·利利斯. (2020). 接纳承诺疗法.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7] 海因茨·科胡特. (1981). 精神分析治愈之道:How does analysis cure?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8] 罗杰斯, C. R. (2013). 当事人中心治疗:实践、运用和理论.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 瓦雷拉, F. J., 汤普森, E., 罗施, E. (2010). 具身心智:认知科学与人类经验.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0] 张松辉. (2024). 帛书老子. 北京: 中华书局.